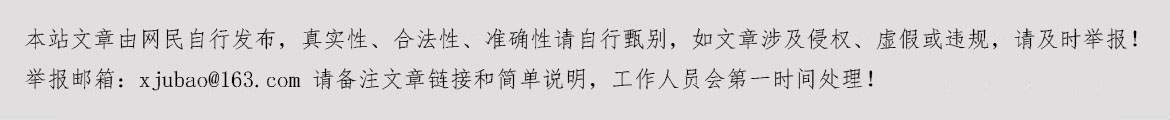(布列松为勒内·夏尔拍摄的人像作品)
勒内·夏尔(René Char),法国诗人,早年投身超现实主义运动,与纳粹抗争的同时举行创作,但坚持在1945年法国解放后才发表。其代表作《恼怒与神秘》被加缪誉为“法兰西诗歌给予我们的惊人之作”,并于1966年入选伽利马“七星文库”经典,在他之前,鲜有作家在世时便获此殊荣。本文选自其中一篇——《情势分享》。
我的姐妹,这便是圣礼之水总在更密切地深入炎天的心。
一
想象力借助欲望富于魔力和颠覆性的气力,致力于把一些不完备的人从现实生活中逐离,以此在一种完全令人满足的进场情势下收获他们的回归。这就是无法熄灭的永存的现实。
二
在诗人与世界的诸多接洽中他所最难忍受的,便是内在公义的缺失。卡利班藏污纳垢的酒瓶背后爱丽儿敏感而万能的双眼射出怒火。*
【注释】卡利班和爱丽儿都是莎士比亚《狂风雨》中的人物。卡利班是普洛斯彼罗收养的一个邪恶怪胎,爱丽儿是普洛斯彼罗召唤的友好精灵。在第三幕第二场中酒醉的卡利班试图挑唆斯丹法诺和特林鸠罗杀死他的主人普洛斯彼罗,在他背后隐身的爱丽儿听到了这统统并深感恼怒。
三
诗人无动于衷地将失败改造成胜利,将胜利改造成失败,他是即将出生的帝王,唯独体贴如何搜集天的蔚蓝。
四
有时诗人的现实生活对于他本人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他不能悄悄地影响其他人对各自现实生活之功业的叙述。
五
操控不宁静性的邪术师,诗人只有领养之满足。余烬始终未到止境。
六
在某一条对我们的欲望而言具有无解妨碍的先决律令闭合的眼睛后面,有时隐藏着一轮姗姗来迟的太阳,它那茴香般的敏感性与我们打仗时剧烈地倾吐香气并把我们环绕。它的温柔所具有的晦暗,它与出人意料的事物间的协约,这极重的高贵对于诗人足矣。
七
诗人必须在守夜的有形世界与就寝可骇的轻松之间保持平衡,他将其诗篇精致的躯体躺卧在字里行间,而这记载其认知的一行行笔墨,不加区分地游走在这些差别生命状态的一端与另一端。
八
每小我私人都会活到把爱补全的夜晚。在一种由全部人配合享有的奇迹调和的威望中,个体的运气完成直至孤独,直至神谕。
九
献给两座丰碑。——赫拉克利特*,乔治·德·拉图尔*,感谢你们恒久以来从我唯一身体的每一处褶皱中推离这骗局:分崩离析的人类处境;感谢你们依据男人的眼光去转动女人裸露的指环;感谢你们使我的解体变得灵动并可堪蒙受;感谢你们为这绝对迫切的光线其不可限量的结果之王冠花费你们的气力:通过被宣告的传统,行动反抗现实,那假象与微缩。
【注释】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535年——公元前475年):古希腊哲学家,行文艰涩、充满隐喻和断片,并对对立物之间的共存举行了极多辩证的论述。在思想和文风上对夏尔影响极大。
乔治·德·拉图尔(Georges de La Tour,1593—1652):法国画家,其作品善于体现黑夜中的灯火与烛光,画作充满张力,在抵抗运动期间给予夏尔深刻的灵感和希望。
十
恰当的做法是让诗与可预见之物形影相随,但尚未加以明确表达。
十一
也许内战是魅人的死亡构筑的鹰巢?哦,痛饮弥留未来的奕奕酒徒。
十二
在绵延的露台上放置与那正在显露的歌之金字塔预定关联的可堪坚守的诗意价值,以此获取这无法熄灭的绝对,这初阳中的枝杈:不可剖析的、尚未得见的火光。
十三
恼怒与神秘已轮替将他诱惑并烧尽。然后完结他虎耳草*之临终的年代到来。
【注释】虎耳草:夏尔对诗人之形象的比喻,又名“穿石草”,由于此种植物习于在石块间穿行并将其崩碎。“虎耳草之临终”表示了诗人曾在“恼怒”与“神秘”之间艰巨地穿行,而现在他终于可以或许对二者同时加以统摄。
十四
在他的酸面包周围转动着再起之时机、重生之时机、雷鸣之时机与镶嵌在圣·阿利尔泉水中的漂游之时机。
十五
在诗歌领域,目前另有几多老手,依然在那坐落奢中原日中的赛马场上,在精心挑选的高贵猛兽中,押注一匹斗牛马,它刚刚被缝合的腑脏因令人作呕的灰尘而悸动!直到那辩证的血栓——它击打统统以敲诈方式构想的诗篇——在这令人无法容忍的用词不妥的作者身上施行公义为止。
十六
诗篇始终与或人结婚。
十七
赫拉克利特夸大了对立物令人激动的联姻。他在其中起首看到了调和产生的完善条件和必备动机。在诗歌领域,当这些对立物相互融合,时而会涌现一种没有明确因由的打击,在这其中令事物溶解[8]的孤独行动引发了深渊的滑动,这一条条深渊以极其反物理的方式承载着诗篇。诗人的责任便是在干预时切断这一伤害,或而通过某种由可靠理性验证过的传统元素,或而借助某种可以破除从因由到结果之整条路径的奇迹般的创造力之火。于是诗人得以真正看到对立物——这些纷繁的局部幻景——结出硕果,看到它们内在的谱系人格化,诗与真,正如我们所知,始终是一对同义词。
十八
和缓你的忍耐吧,王子的母亲。就像昔日你曾帮助抚养被压迫者的雄狮。
十九
属于雨季的成人与属于晴天的孩子,你们的失败与进步之手对我而言同样须要。
二十
透过你火红的窗口,请从这纤细柴堆的轮廓里认出诗人,他是燃烧的成堆芦苇并由出乎意料的事物所簇拥。
二十一
在诗歌领域,只有从事物全体性的交流相同与自由结构出发,在二者之间穿过我们,才能让我们感到投入与确定,从而得以获取我们独创的情势与可堪检验的特性。
二十二
成年时我在分开生死的墙壁上看到一把愈加赤裸的云梯直立和增长,并被赋予一种奇特的萃取能力:梦。它的踏板,从某一处进睁开始,不再支持积攒就寝的平滑储户。被人为注入的思想深度的杂乱空缺,其中的杂乱形象为一些充满天赋但无力估量脚本普遍性之人的审判庭*充当园地,在此之后,晦暗便开始扩散而生活,在一种充满寓意的严酷苦修情势下,成为对非凡能力的征服,我们感到已被这些能力充实贯串但却只能不完备地表达自己对于正直、对于严厉的判断力和对于恒心的缺乏。
话不成声的悲怆同伴,请你们拿走熄灭的灯并交还珍宝。一种全新的秘密在你们的骨骼中歌唱。请发展你们正当的奇思。
【注释】此处表示了夏尔对超现实主义团体首脑安德烈·布勒东的品评,后者曾不停地把各种与他理念不合的同伴开除出超现实主义团体。
二十三
我是诗人,枯井的搬运工,而你的远方,哦,我的爱人,供应着食粮。
二十四
通过一种高强度的体力劳感人们得以在近似室外的冷气中坚持,并使人们消除被其吞没的伤害;因此,当我们回归非己所愿的现实,当我们把诗篇的血脉交付于运气的时刻来临,我们发明自己身处一种相似的处境。我们被石化的磨坊水轮——那些瓦砾——开始转动,擦拭低处难以触及的流水。我们的积极重新习得与之相当的汗水。而我们,大地上永不死去的斗士,将走进那些把我们激怒的目击者与冷漠的道德。
二十五
如果去抗拒那虚无所短缺的想象力之水滴,就是专注于把虚无对我们造成的恶耐心地交还永恒。
哦,蝰蛇腹中的月桂瓶!
二十六
死去,这绝不只是强迫他的意识在行将就木之时,去向身躯上的某几个活跃或昏睡的物质区域告别,这具躯体因其知觉只能以吝啬而零星的方式抵达我们,而曾让我们感到相当异样。那是喧嚣中毫无美感的巨大乡村,曾经劳作着控制的住民……而在这严酷的艰涩之上耸立着一根面相佝偻、肿痛、半盲的阴影之柱,每隔一段——哦,何等幸福——被雷电割下表皮。
二十七
恐怖、精致又游移不定的大地,与异质的人类状态相互攫取并相互定性。诗意便从它们织物的活跃整体中得到提取。
二十八
诗人是具有单侧稳定性的人。
二十九
诗篇从一种主观的强制和一种客观的选择中浮现。
诗篇是一场具有决定性原创价值的移动集会,这些价值与由这一情势开始造就之人共时相干。
三十
诗篇是由依然延续为欲望的欲望所实现的爱。
三十一
一些人为了她请求延期穿上甲胄;他们的伤口带有一种永恒折磨导致的哀愁。然而诗,她用她芦苇与砾石的双脚赤裸地向前走去,没有听任自己在任何地方遭到缩减。女人,我们在她那紧靠天顶蟋蟀的唇间亲吻疯狂的韶光,她歌唱冬夜,在破旧的面包店里,在光之面包的芯中。
三十二
诗人不会为死亡丑陋的寂灭而动怒,却信托它那非同寻常的碰触,将万物转化为绵长的羊绒。
三十三
当他在语言普遍性的垦荒地里行动的历程中,廉正、贪心、善感又冒失的诗人将警惕自己对某些可以或许异化诗歌中自由之奇迹的事业产生同感,换句话就是警惕生活中的机巧。
三十四
一个被人们忽略的生灵是一个无穷而敏感的生灵,当他参与进来,便能把我们的焦虑与重负转化成动脉般的晨曦。
在无知与有知之间,在爱与虚无之间,诗人每一天都在铺展他的康健。
三十五
当诗人把他的意图转译成充满灵感的举动,把劳苦的循环折换为复生之货柜,他便通过疲劳之玻璃上的每一个气孔进驻凉气的绿洲,而且创造一面棱镜,区分积极、奇异、严厉与洪灾的九头蛇,把你的双唇看成智慧并把我的血液看成屏风。
三十六
诗人的寓所最缥缈无迹;一道悲伤的火焰旋涡受命于他的白木桌。
诗人的活力不是某种彼岸的活力,而是一个闪耀钻石光辉的由逾越性的在场与暴雨中的朝圣者组成的当下的焦点。
三十七
我能否拥有交互的面目面貌只取决于你预支于我的爱欲的须要性。
三十八
刚刚掷出的骰子,无法握住的骰子,由于它们是诞生与朽迈。
三十九
在重力的门槛上,诗人恰似蜘蛛在空中构筑他的门路。在他奇谋的范围内,他局部地隐匿自己,却在别人眼中致命地显见。
四十
与诗篇一同穿越沙漠的牧歌、狂怒人格的天禀与因眼泪而发霉的火。紧随诗篇的脚跟奔跑,向它祈祷,把它唾骂。将它等同为其天赋的表达以致被其贫瘠压垮的卵巢。借着夜色,冲入它的套房,终极,在宇宙间石榴的婚礼中。
四十一
在诗人体内包罗着两种事实:第一种以外部现实所掌握的多样化情势立即给出其全部意义,它难以向下深挖,仅仅就事论事;第二种被嵌入诗篇之内,它讲述栖息在诗人身上的那些强盛而任性的诸神发出的命令与论述,一种不会枯萎或熄灭的硬化事实。它的支配权是一种给予。当被说出,它占据着一片面积可观的疆域。
四十二
作为诗人,就是对某种不安产生食欲,在现存与预期的全部事物的旋风中,他对这种不安加以使用,并在终点处,引发至福。
四十三
诗篇从它的总量中吸收并给予那从其密室内逐出的诗人全部的表达方式。在这血染的百叶窗后某种气力的尖啸在燃烧,这种气力只会摧毁它自己由于它讨厌暴力,它主观而贫瘠的姐妹。
四十四
诗人借助深不可测的秘密不停拷打其喷泉的情势与音响。
四十五
诗人是一个向外投射的生灵与一个向内扣留的生灵的配合起源。他向情人借得空虚,向爱人取得光线。这一对情势组合,这双重的保镳悲怆地给予诗人他的嗓音。
四十六
坚定地坐在他的柏树帐篷下,诗人,为了自我说服并自我引导,不能畏惧使用统统跑进他手中的钥匙。然而他也不能混淆界限的喧闹与革命的远景。
熟悉两类可能性:白昼的可能性与违禁的可能性。如果可以,让前者与后者对等;把它们放置在不可能性的皇家大道上,这种充满魅力的不可能性是最高层级的可理解之物。
四十七
诗人要求:“请你弯下腰,请你更深地弯下腰。”他并非始终平安无事地竣事他写下的篇章,但就像穷人一样他知晓如何从一颗橄榄中提取永恒。
四十八
面临质据的每一次坍塌,诗人用未来之齐鸣加以回应。
四十九
任何呼吸都提出一次统治:胶葛之使命,维护之刻意,恢复自由之热情。诗人在纯洁与贫苦中分享着一部门人的生存状态,非难并抛弃另一部门人的武断专横。
任何呼吸都提出一次统治:直到这颗为了在无穷中打碎自己而哭泣、坚持并解脱的单一类型的头颅,这颗由想象之物组成的断头之运气得以完成。
五十
人类处境的某些时期忍受着某种恶酷寒的侵袭,这种恶在人类天性最松弛处寻得依赖。在这场飓风的中心,诗人将通过对自我的拒绝去补全其留言的意义,然后加入如许一群人,他们剥夺了苦难正当性的面罩,正在确保那顽强的脚夫,正义之摆渡者的永恒回归。
五十一
这座通过其每一道暗门播撒自由的堡垒,这根在空中保持着一个具备普罗米修斯式远见的躯体同时由雷电照亮并回避的蒸汽草叉,这就是诗篇,献给过分的任性,在一瞬间将我们捕捉然后消散。
五十二
在交付其珍宝(它们在两座桥之间盘旋)并抛洒其汗水之后,诗人,身体的半边,未知中灵感的顶峰,诗人不再是对某个完成事件的反应。不再有任何事物可以把他权衡或束缚。清朗的都会,闭锁的都会在他眼前。
五十三
直立着,在延续的时间中生长,诗篇,是神秘登位。一旁,沿着大众葡萄园中的小径,诗人,巨大的起始者,不及物的诗人,身处其静脉光辉的任意何人,诗人从自身的深渊中提取恶运,随同他身旁的女子一起探寻稀世的葡萄。
五十四
这小我私人,从里到外反抗着那入骨的贪心嘴脸令他熟知的恶,他无疑有责任去把传说的事件转化为汗青。我们不安的信心不应把他诋毁而要对他讯问,我们,这些把真实的生灵们消灭在我们幻想出的绵延人影中的激情亲切屠夫*。间接的邪术,敲诈,现在依然黑夜无边,我身体不适,但统统重新开始运行。
带着诗无边的展望逃向他的同类,也许有一天将成为可能。
【注释】此处意为诗人像杀手一般把身边活生生的人转写成一系列充满幻想、梦乡或理念的笔墨,从本质上戕害了他们真实的存在。
本文节选自